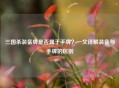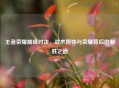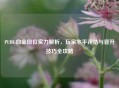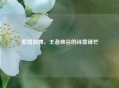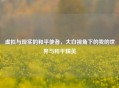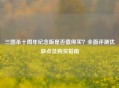1907年7月15日凌晨,绍兴轩亭口,一位身着白衣的女子在晨曦中昂首挺立,当刽子手的刀光闪过,秋瑾的生命定格在三十一岁,但她以生命为代价跳完的那支"革命之舞",却在历史的长廊中激荡出永恒的回响,这位被后世称为"鉴湖女侠"的奇女子,用短暂而璀璨的一生,在晚清腐朽的舞台上完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逆战之舞——她以笔为剑,以血为墨,在封建礼教的铜墙铁壁上撕开了一道裂缝,让新思想的阳光照进了千年黑暗。
秋瑾的舞蹈始于对命运的反叛,出生于官宦之家的她,本可安享富贵,却在二十岁那年毅然挣脱包办婚姻的枷锁。"身不得,男儿列;心却比,男儿烈"——她在《满江红》中的呐喊,是对性别宿命的宣战,东渡日本后,她剪去长发,身着男装,手持短刀拍照,这些惊世骇俗的举动不是哗众取宠的行为艺术,而是一个觉醒灵魂对封建礼教最激烈的舞步,在东京留学生会馆,她创办《白话报》,用通俗语言向民众传播革命思想;在横滨,她加入同盟会,将柔弱的女性躯体锻造成革命利器,这些看似"离经叛道"的举动,实则是她在时代悬崖边上跳出的最壮美的舞姿。

秋瑾的革命之舞充满令人战栗的美学张力,1906年,她在上海创办《中国女报》,发表《敬告姊妹们》一文,字字血泪:"诸位姊妹,天下最苦最痛的事,莫过于我们女子了。"这种将个人痛苦升华为群体觉醒的能力,使她的文字具有穿透时空的力量,在主持大通学堂期间,她白天教授文化课程,夜间秘密训练革命军,这种双面人生恰似舞蹈中的旋转——一面是温文尔雅的女教师,一面是叱咤风云的革命家,起义失败被捕后,面对严刑拷打,她仅写下"秋风秋雨愁煞人"七字供状,这种沉默胜过千言万语的抗争姿态,构成了她生命之舞最凄美的收势。
这位革命舞者的精神律动至今仍在历史中回响,在绍兴古轩亭口,秋瑾纪念碑巍然矗立,上面刻着孙中山亲笔题写的"巾帼英雄",但比石碑更不朽的,是她用生命诠释的革命辩证法——真正的变革从来不是请客吃饭,而是需要以头撞墙的勇气,当下社会虽无血与火的考验,但各种形式的压迫依然存在,秋瑾教会我们,面对不公,最优雅的姿态不是委曲求全,而是昂首挺胸地"跳舞",这种舞蹈可能是为弱势群体发声,可能是坚守职业操守,也可能是对真理的不懈追求,每个时代都需要自己的"秋瑾",用不同的方式完成属于这个时代的逆战之舞。
百年回望,秋瑾的生命如同一把出鞘的宝剑,在黑暗中划出炫目的光痕,她证明了一个人可以用三十一年光阴活出三百年的价值,证明了柔弱身躯里可以迸发出改变历史的力量,在这个容易随波逐流的时代,我们更需要重温秋瑾的舞步——那种明知必败却依然奋起抗争的勇气,那种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前途紧密相连的胸怀,也许,对这位革命舞者最好的纪念,不是将她供奉在神坛,而是让她的精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复活,继续那支未跳完的自由之舞。